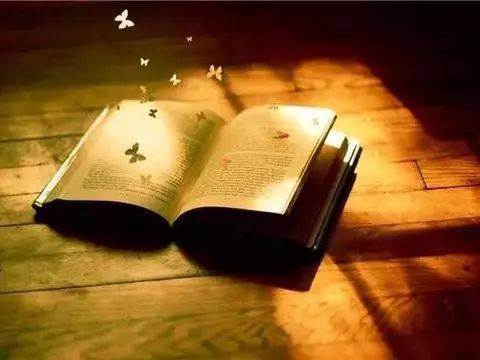
大约在我五六岁时,外婆几乎每个月必牵着我的手到南市大南门看望她姐姐的养子,一个癫痫病人。表舅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,据说是经常跌跤摔的。每每见面我叫舅舅,他总是慌慌忙忙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卷带体温的水果糖或桉叶糖。外婆总是问他生活琐事,最多的是问表舅妈对他好不好,外婆是替她去世的姐姐主持公道。我呢,总觉得表舅的眼神怪怪的,与人不同。
1972年,我一个大队的插兄突然得了类风关节炎,从安徽回上海,住在医院里治病。我和他既是邻居,又是他妹妹的小学同班同学。他那个眉眼如工笔画的妈妈和妹妹来我家请我替他们家写信,向公社五七办公室要医药费。同学的妈妈还塞给我弟弟四块萨其马。这,大概是我人生第一笔稿费吧。他们家太困难了,爸爸在福建工作,妈妈在里弄加工厂糊纸盒,三个孩子两个下乡,唯有我同学在家待业。我虽囊中羞涩,还是买了几只苹果和我同学一起去看望他。隆冬时节,特别冷,医院没有暖气,平添了几分凄凉,相对无言,病人躺在病床上,面黄肌瘦。他再三谢我,怪我不该买苹果,我只说回去就去公社要医药费。告别之际,我发现他的眼神与当年表舅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那天,我读懂了那眼神:一个病人无助、忧伤、恐惧的心理写照。
说来可怜,两年后这位插兄与世长辞了,好像刚过二十岁。
去年,我先生得了肠癌,第三次化疗,医生要他空腹验血。先生还是个有二十几年糖尿病史的糖尿病人。医院床位紧张,前面的病人慢条斯理不早早去办出院手续,只能耐心等待。天阴冷阴冷,3号楼楼道四面透风,先生,昏迷了,满眼是泪地叫他没反应。想让他到住院部去喝一口热水,蹭一点暖气,可是用尽力气,他一步都不动。好心的病人家属劝我去借轮椅。奔到10号楼,因为没有身份证作抵押,被值班护士长拒绝,苦苦哀求无效,那个长得美美的小护士居然说:“别理她,她就想把病人弄上来赖我们身上。”我不擅长吵架,仅说了一句,我是个教书的赖你们什么。哀求无门,吵架无术,恨恨地离开,终于,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把昏昏沉沉的先生拖到10号楼。
恶言一句三春寒,美小护的话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。视患者如虎,也许忘却了虎守杏林的经典传说。不知怎的,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在我脑中闪现。自然,我无李斯的文采,不然直书胸臆,仿写一篇“医患关系书”,许也能感动天下好心人。其实,书,中科院韩院士已经写了,他用亲身经历身体力行的感受写了一本好书,精髓当是:“医学是人学,医学是有温度的。”然而,谁解其中意?
我,为了那个无助、忧伤、恐惧的眼神,曾为插兄去公社五七办公室要医药费,被人讽刺;曾为他开了我人生第一场拍卖会,把他的家当变成了现金,把34.8元和一顶蚊帐寄回他家,那年我十八周岁。我曾经两次无偿献血,2006年第二次献血时,我已五十三周岁了。我想:我的血能帮助几个人,值了。(陈嘉芬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