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社会支持系统简直无懈可击”
我是大一确诊的抑郁症,那年19岁,现在我25岁。但在我很小的时候,抑郁的种子就已经埋下。
我三岁时,因为爸妈要外出工作,我在亲戚家里寄养了半年,性情因此大变,有一个事很能反映我当时的处境,亲戚的家里有一儿一女,和我差不多大。有一次,我在幼儿园因为上课认真,被老师奖励了一个很漂亮的笔筒。结果当我高兴地把笔筒带回去后,就被亲戚的女儿直接拿走,放到她的桌子上了。我当时很伤心,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,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在,没有人为我撑腰。
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,让我从一个活泼的小孩变得安静内向、不爱讲话。我还养成了讨好型性格,比如,在学校,同学说句我喜欢天蓝色,我会说我也喜欢天蓝色,因为我很害怕跟他们不一样。
但整体来说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还算顺利。直到大一,因为一个导火索,彻底爆了。当时,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恋爱、分手,招来了一些风言风语。有一次,我一回到宿舍,几个舍友故意当着我的面念我和那个男生的聊天记录,一边念一边笑,我才知道,在此之前,男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我交流,就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发给其他人看,想让他们支招,其实是个很正常的操作,但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我的舍友手里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的所有心思和隐私被暴露在众人面前。

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剧照
也是从那时开始,我变得不正常。比如,比如,走在路上时,我老是觉得,别人在笑话我。我的思维变得很迟钝,别人说一句你吃饭了吗?我都要想好久才能反应过来。我读的是会计专业,上课时,我发现脑子好像挂了铅一样难以运转。我也有躯体化症状,比如背会很僵硬、很痛。大一暑假,我确诊为重度抑郁。
当年的11月底,我休学了。这时候就要感谢医生给我的建议,他让我尽量继续留在学校,否则,一旦脱离,我会很难再融入那样的环境。所以,休学的那一年,我仍泡在学校,这对我后来的康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虽然不上学,但学校很包容我,除了进不去图书馆,一切资源仍对我开放。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,继续每天去学校通勤。没有了学业压力和人际困扰,我的生活反而开始丰富起来,大一时,我参加了学校的国学社,听说我休学后,他们也不问我原因,只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参加十佳社团的比赛。
这个社团比较核心的成员有差不多十几个,从大一到大四的都有。我们一周有一次聚在一起的时间,隔两周还会举办文化集市,摆摊儿展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小玩意,比如泥塑、纸鸢、等等。其他时间里,我们就一起吃吃喝喝、开party,唱歌,郊游,正常大学生的一切业余活动,他们都带着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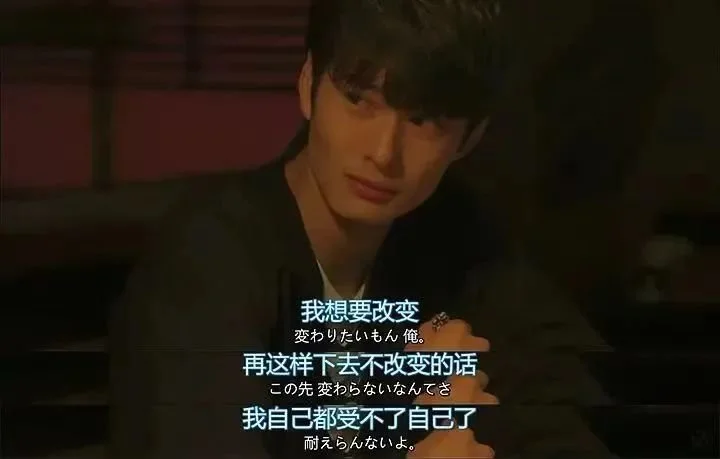
《宽松世代又如何》剧照
我又在学校的表白墙莫名其妙认识了一些人,比如,有一个女生在学校的告白墙发通告,想搞一个民乐团,当时我正好在学古筝,就去加她,手机上一聊才发现,她正坐在我前面,是我的学妹。当时她刚遇到宿舍矛盾,也是状态最糟糕的时候,我们俩就坐在小花园里聊了很久,缘分很奇妙,后来,我打算复学,她要换宿舍,我们俩又变成了舍友。
这些新认识的朋友就扮演了倾听者的角色。那段时间,我几乎跟认识的每个人都讲过我和那位男同学的情爱瓜葛,大学生是很爱听这种故事的,当然生病的部分被我隐藏了。我发现,讲着讲着,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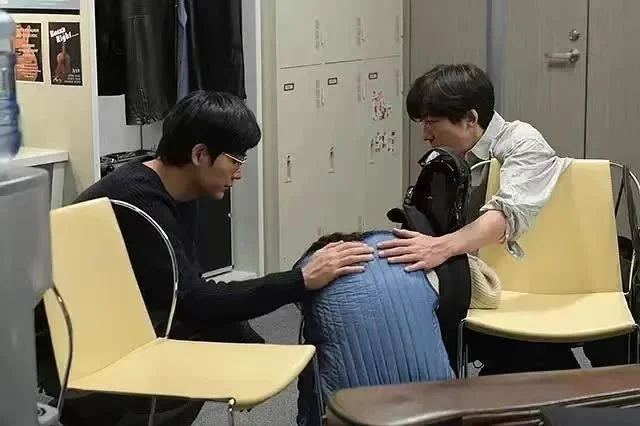
《四重奏》剧照
当大家对我的病情多少有点了解后,变得更关心我,有时看我把头像换成黑色,就会有一堆人来问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。发展到后面,每天都会有人问我,今天要不要出来喝个茶,吃个饭,我们把厦门玩了个遍,学校附近的小吃街基本上也被我们吃过一遍。他们点亮了我的生活。
可能因为我们都是95后一代,对抑郁症的认识比较充分,更没有羞耻感。最离谱的是,当我跟他们讲我的病情,他们也会把自己之前经历的创伤告诉我,还有朋友直接问我,“我这样子算抑郁情绪还是算抑郁症?要不要去医院?”最后变成了互相疗愈。
后来我想,我能康复,是多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效果,一是朋友的陪伴,二是我坚持吃药,看医生,我也愿意相信医学,三是父母的支持,四是学校对我挺包容。我在学校有一个心理咨询师,他陪伴了我两三年。后来我加入心理疾病患者互助康复社区渡过,群友们也很羡慕,说我的社会支持系统简直无懈可击。
